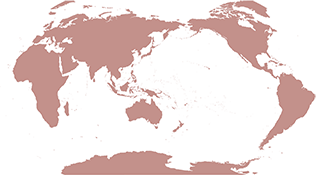
半月談?dòng)浾撸簭堄駶?任延昕
世人皆知,敦煌莫高窟是世界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延續(xù)時(shí)間最長(zhǎng)、內(nèi)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藝術(shù)寶庫。只是,大家也許不會(huì)注意,莫高窟的文物也自有其“壽命”。壽數(shù)有限的寶貴文物,如何傳承下去?今日敦煌研究院的學(xué)者們,給出的解答是——以數(shù)字化技術(shù)讓敦煌文物以更完整、更多樣的形態(tài)光彩重生。
壁畫“老”了,怎么辦
20世紀(jì)70年代末,時(shí)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副所長(zhǎng)的樊錦詩發(fā)現(xiàn),對(duì)照文物保護(hù)單位“有保護(hù)范圍,有標(biāo)識(shí)說明,有專門機(jī)構(gòu)管理,有科學(xué)的記錄檔案”的“四有”要求,敦煌尚未為文物建立科學(xué)檔案。于是,她組織編制敦煌石窟檔案,每本檔案“至少要有6張記錄照片”。
對(duì)比法國(guó)人伯希和1908年拍攝的莫高窟照片,樊錦詩發(fā)現(xiàn),70多年后拍下的壁畫彩塑,已經(jīng)不如七八十年前那樣清晰和完整。而檔案照片及其膠片,也會(huì)隨著時(shí)間推移而變色變質(zhì)。
樊錦詩回憶:“這次做檔案和查舊檔,我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在衰變、退化。如果石窟文物繼續(xù)衰變、退化,敦煌石窟是不是最終會(huì)消亡呢?”
這樣的憂思縈繞在樊錦詩心頭。后來,她去北京出差,偶然看到有人在電腦上展示圖像。回憶起當(dāng)時(shí)的靈光一現(xiàn),樊錦詩仍很興奮:“當(dāng)?shù)弥獔D像數(shù)字化后儲(chǔ)存在電腦中就可以永遠(yuǎn)不變,我想到,如果為敦煌石窟建立數(shù)字檔案,文物的歷史信息豈不就可以永久保存了嗎?”
初試數(shù)字化
這一想法,得到當(dāng)時(shí)甘肅省科委(現(xiàn)甘肅省科技廳)的支持,專門為敦煌研究院立項(xiàng)撥款30萬元,用于敦煌石窟數(shù)字化檔案建設(shè)試驗(yàn)。于是,敦煌研究院在全國(guó)文物界率先開始了數(shù)字化探索。
不同于可移動(dòng)文物,莫高窟已經(jīng)在大漠靜靜佇立千余年,735個(gè)洞窟如蜂巢般排布在崖壁上,大小不一、形制多樣、結(jié)構(gòu)復(fù)雜。光是洞窟形制,就有中心塔柱、覆斗頂、人字披頂?shù)榷喾N類型。其中最大的一幅壁畫——莫高窟第61窟《五臺(tái)山圖》,長(zhǎng)達(dá)13米,高度超過3米,面積約有半個(gè)羽毛球場(chǎng)那么大。
如何應(yīng)對(duì)如此復(fù)雜的文物本體條件和周邊環(huán)境?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探索近10年,苦無良策。到了20世紀(jì)90年代,得到美國(guó)梅隆基金會(huì)的支持,敦煌研究院與美國(guó)西北大學(xué)合作,引入了基于軌道系統(tǒng)的覆蓋式壁畫采集和圖像拼接相結(jié)合的壁畫數(shù)字化技術(shù)。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hù)團(tuán)隊(duì)成員在查閱“數(shù)字敦煌”資源庫 陳斌 攝
“像拍電影一樣架設(shè)軌道,讓照相機(jī)以正投影方式移動(dòng)拍攝,再把照片拼接起來。”樊錦詩回憶。
2005年底,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22個(gè)典型洞窟的數(shù)字化采集工作終告完成,還制作了5個(gè)基于QuickTime VR技術(shù)的虛擬漫游洞窟。
借助中外合作,敦煌石窟數(shù)字化保護(hù)工作走過了最初階段。敦煌研究院文物數(shù)字化研究所副所長(zhǎng)丁曉宏回憶,當(dāng)時(shí)數(shù)據(jù)采集精度僅有75DPI,且受限于計(jì)算機(jī)和軟件基礎(chǔ)性能,數(shù)據(jù)質(zhì)量和采集效率不高。
從摸索方法到建立標(biāo)準(zhǔn)
2006年,敦煌研究院成立數(shù)字中心,2014年更名為文物數(shù)字化研究所,工作重心是探索文物數(shù)字化的自主化道路。
“早期,我們使用在美國(guó)定制的數(shù)字化采集設(shè)備,成本高昂、維護(hù)麻煩。后來,我們與浙江大學(xué)等國(guó)內(nèi)高校聯(lián)合攻關(guān),逐步實(shí)現(xiàn)采集裝備自主研發(fā)集成。”丁曉宏說,目前中心的自動(dòng)化采集設(shè)備已更新至第四代。根據(jù)敦煌石窟洞窟大小不一、形制多樣的特點(diǎn),他們還設(shè)計(jì)了多種規(guī)格尺寸的軌道和配套附件,滿足不同空間內(nèi)的工作需求。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hù)團(tuán)隊(duì)圖像采集人員在洞窟內(nèi)調(diào)試設(shè)備,準(zhǔn)備進(jìn)行壁畫圖像采集 陳斌 攝
如今,敦煌石窟數(shù)據(jù)采集精度從75DPI提升到300DPI,年采集洞窟數(shù)量從一兩個(gè)增至二三十個(gè),所獲數(shù)據(jù)可直接滿足出版印刷、展覽展示的需求。這意味著在屏幕上呈現(xiàn)的壁畫清晰度遠(yuǎn)超實(shí)地觀賞,那些以往需攀梯細(xì)看的壁畫細(xì)節(jié),如今能輕松走向世界。
經(jīng)過多年實(shí)踐,敦煌研究院摸索出一整套不可移動(dòng)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hù)的工作流程規(guī)范,現(xiàn)已成為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2024年7月1日,由敦煌研究院牽頭起草的國(guó)家文物保護(hù)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石窟寺二維數(shù)字化采集與加工》《石窟寺三維數(shù)字化采集與加工》正式實(shí)施,填補(bǔ)了我國(guó)石窟寺數(shù)字化保護(hù)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的空白。
“再造”數(shù)字洞窟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經(jīng)完成敦煌石窟中300個(gè)洞窟的高精度數(shù)字化采集工作,同時(shí)為212個(gè)洞窟做了結(jié)構(gòu)三維掃描,并制作了169個(gè)洞窟的全景漫游。在這些工作的基礎(chǔ)上,于數(shù)字世界中“再造”莫高窟,道路已經(jīng)展開。
2016年、2017年分別上線中、英文版“數(shù)字敦煌”資源庫,首次實(shí)現(xiàn)敦煌石窟30個(gè)洞窟整窟高清圖像的全球共享;2022年,“數(shù)字敦煌·開放素材庫”上線,6500余份敦煌數(shù)字資源首次開放下載;2025年,“數(shù)字藏經(jīng)洞”數(shù)據(jù)庫平臺(tái)上線,集納敦煌文書經(jīng)卷9900多卷、圖像60700多幅……
特別令海內(nèi)外敦煌研究學(xué)者欣慰的,是“數(shù)字藏經(jīng)洞”數(shù)據(jù)庫平臺(tái)的上線。都知道敦煌不僅有石窟,還有另一座文物寶庫藏經(jīng)洞,而藏經(jīng)洞出土的7.3萬余件各類文物,有4.7萬余件流散海外。近年來,敦煌研究院積極推進(jìn)“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數(shù)字化復(fù)原項(xiàng)目”,在國(guó)際敦煌項(xiàng)目的基礎(chǔ)上,“數(shù)字藏經(jīng)洞”數(shù)據(jù)庫平臺(tái)逐步成型。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hù)團(tuán)隊(duì)圖像處理人員在拼接壁畫圖像 陳斌 攝
這一平臺(tái)整合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目錄、珍貴圖像,并納入海量國(guó)內(nèi)外敦煌學(xué)研究成果,同時(shí)運(yùn)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自動(dòng)識(shí)別經(jīng)卷文字,具備圖像拼接、圖像綴合、知識(shí)圖譜構(gòu)建、全文檢索等多項(xiàng)功能。
“我們初步搭建了一個(gè)集藏經(jīng)洞經(jīng)卷、敦煌學(xué)研究資料于一體的資源管理和全球共享平臺(tái),為社會(huì)呈現(xiàn)了一座貫通古今的敦煌千年數(shù)字圖書館。”敦煌研究院院長(zhǎng)蘇伯民說。
不斷豐富的數(shù)字化應(yīng)用,也改變了公眾與文物的相遇方式。
當(dāng)游客步入莫高窟,拿出手機(jī),身披絲帶的九色鹿從壁畫中“飛身而下”,還會(huì)輕扭身體,與人互動(dòng)。走進(jìn)“尋境敦煌”展覽,佩戴好VR設(shè)備,“飛”起來看洞窟的夢(mèng)想就能成真。高捧蓮花的飛天、手敲連鼓的雷公、邊飛行邊降雨的雨神……眾神觸手可及。
千年敦煌,正在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扶助下,在更廣大的世界中煥發(fā)活力,望向文明更為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