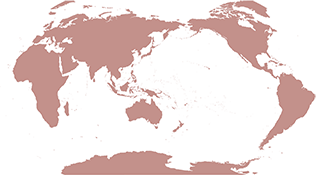
首都師范大學校園欺凌國際研究中心 張倩
近年來,惡性欺凌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傷害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沖擊著社會道德底線。社會各界對此義憤填膺,一時之間,要求“嚴懲”的呼聲不斷,下調刑事責任年齡成為網絡媒體中案件討論的主流聲音。
懲惡是保障未成年人利益、維護社會正義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從學生欺凌治理的角度來看,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法治是最后的底線。換言之,僅僅依靠法律手段對欺凌者進行事后的懲治,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學生欺凌行為的發生呢?其實這是擺在世界各國政府面前共同的挑戰。作為最早對學生欺凌進行防治干預的國家,也是國際上欺凌防治經驗和研究的主要輸出國,挪威對學生欺凌及其治理問題的認識和做法,對我們當前的欺凌防治工作還是有所啟發的。
挪威強調,首先應該站在生態系統理論的角度來認識學生欺凌問題,即學生欺凌不是孤立的個體問題,也不是隨機的行為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復雜社會系統里的多個要素互動的產物,反映的是特定環境內的復雜的社會互動關系。僅僅在事后對欺凌者進行懲罰,其效果無異于撲山火。只要引發山火的干燥易燃環境不變,山火就可能隨時爆發。換言之,若不改變導致學生欺凌行為產生的社會生態環境,那么懲處一起,還會有下一起。而且社會生態環境的形成是漸進的,若不極力扭轉,往往會呈穩態化趨勢,屆時學生欺凌極有可能呈現多發態勢。因此,從本質來看,治理學生欺凌就是對導致欺凌行為產生的社會生態環境進行治理,而不僅僅是針對個體和事件本身進行事后干預。
從生態系統理論角度看,個體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可以劃分為四層次的嵌套系統:小環境系統、中環境系統、外環境系統和大環境系統。其中,最里層的小環境系統對個體發展的影響最為直接而頻繁,構成個人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生活場所。近年來多起惡性欺凌事件也反映出一個共性特征:涉事學生往往在家庭中得不到足夠的關愛和監護。影響孩子發展的小環境系統里,除了家庭,還包括同伴、教師、班級、學校等。已有研究發現,同伴關系、教師對待欺凌的態度、班級和學校為個體提供的社會支持等都對欺凌卷入具有一定預測性。同伴關系不良、教師對待欺凌持“容忍”或“忽視”態度、班風差、對學校持弱歸屬感的學生,往往更容易卷入欺凌。中環境系統是由小環境系統里的微系統互動而形成的,比如家校互動、學校與社區的互動等。
在這兩個核心層次之外,是與學生個體行為發展沒有直接互動關系的遠端社會因素構成的外環境,比如國家和地方的教育行政系統、社會福利系統、大眾傳媒、國家司法、社會團體、教師教育等。最外圍的大環境是指由社會道德、文化、習俗和法律構成的系統,它決定了各子社會系統的基本立場和運作方式。如在我國許多地區,包括農村,手機已成為初中學生的必備品,其結果就是尚不懂分辨是非的孩子過早地充分暴露在泥沙俱下的網絡文化中。當孩子生活在充滿暴力和低俗、缺少包容和理解的環境中,他們更有可能從周圍環境和網絡環境中學習暴力行為,那么欺凌等行為的發生幾率也會隨之提高。
學生欺凌是復雜的社會問題,它的有效乃至長效的治理,絕不可能停留在對欺凌者嚴懲的單一干預層面,也不可能僅僅依靠一次運動、一次摸排、一個部門,甚至不能僅僅依賴政府的行政資源,而是需要更多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和持續努力。因此,欺凌事件的發生,喚醒的不應只是全民對受欺凌者及其家長的同情與共情,更要喚醒的是全民對欺凌防治工作的責任意識和參與意識。只有各級政府、學校和家庭、研究機構、社會各界各司其職,以不同的功能角色和行為方式參與到學生欺凌治理工作中,我們才可能為所有孩子創造一個對欺凌“零容忍”的社會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