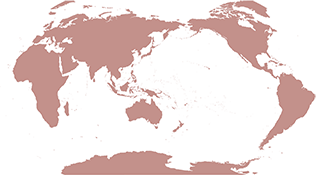
半月談記者 周思宇 俞菀
近期,商務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九部門發文,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結合氣候條件、生產安排、職工帶薪休假制度落實等因素,科學調整每學年的教學和放假時間,探索設置中小學春秋假,相關話題迅速登上熱搜。中小學春秋假,怎么才能放得安心、放得精準、放得有意義?
多地已探索實施春秋假
春秋假,是指在保證全年總教學時長不變的前提下,在春季和秋季分別增設一個短假期,區別于傳統的寒暑假。在已實施的地方,春秋假通常與“五一”“國慶”等法定節假日銜接,以形成更長的連續休息時間,便于學生放松身心、參與實踐活動或家庭出行。
早在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中就曾提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學春秋假。西南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王正青告訴半月談記者,從經濟社會層面看,春秋假為更多家庭提供了錯峰旅游出行的機會,有利于拉動內需、優化文旅資源配置、推動服務消費擴容提質;從制度創新層面看,春秋假往往與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并列提出,有利于完善假期結構與社會休假制度;從教育發展層面看,春秋假能有效緩解學生長學期連續學習帶來的壓力與疲勞,給予學生更多走近自然的研學和社會實踐機會,有利于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

據介紹,杭州2004年正式實施中小學春秋假,是我國最早探索設置春秋假的城市。“在具體實施上,我們不搞‘一刀切’,而是不斷聽取各方意見來調整完善。”杭州市教育局黨組成員、總督學孔永國介紹,20多年來,根據各方反饋,杭州的中小學春秋假逐漸調整并固定:春假一般安排在4月底,與“五一”假期連休;秋假則多安排在9月底,與國慶假期銜接。今年,杭州還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春秋假實施的通知》,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免費春秋假托管服務。
據了解,目前浙江已在全省推行中小學春秋假,廣州佛山、湖北恩施等地也先后進行春秋假試點。在高校中,中國人民大學、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等均已試行春秋假。
放假誰來帶娃?家長喜憂參半
假期調整涉及社會、家庭等方方面面。對于中小學春秋假,大多數家長認為春秋假可以紓解學業壓力,對孩子的成長發展有利,但還有不少家長擔憂自己沒有配套假期,無法兼顧工作和照顧孩子。
“有了春秋假,能在不同季節帶孩子出去玩一玩、走一走,對他們的成長還是很有必要的。”重慶一名幼兒家長王先生說,“我們家老人身體都還比較好,能幫忙帶娃,所以我支持放假。”
“現在孩子學習壓力確實太大了,放假讓孩子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家長安先生說,不過最好別放假,“我們工作本就很忙,沒有配套假期怎么帶娃?孩子放假只能待在家里,最多就是看看電視,玩玩手機和平板”。
“我很喜歡春秋假,如果爸爸媽媽有空的話,我們就能外出旅游。如果爸爸媽媽沒空,我可以跟著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去鄉下體驗生活。”杭州市西湖小學一名學生說,“學校有托管班,可以到學校把作業做完,也有同學報名去外地的研學項目。”
杭州市文一街小學學生家長諸先生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是支持春秋假的,孩子很喜歡,學校也有托管的兜底政策,而且是免費的。“班上近1/3的家長因請假困難選擇托管服務,絕大部分學生因各種原因表示不會選擇出游。”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團初中部教師費丹艷深切感受到春秋假落地的現實阻力。

多方合力讓春秋假真正發揮作用
王正青認為,要讓春秋假真正發揮作用,需要多方面支持。一是財政支持,補貼學校春秋假配套資源配置,提供校內托管與集體實踐活動補助。二是社會支持,建立學校與社區共同參與的托管和公益活動體系,解決“沒人帶娃”的現實困境。三是監管支持,堅持減負導向,嚴禁布置過量作業;對社會實踐和相關研學活動實行準入備案、安全保障和保險全覆蓋,同時建立公開透明的收費標準。
受訪者表示,要使中小學春秋假成為素質教育的有效延伸,需將假期規劃、活動設計與社會支持緊密結合。如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團編制了《青春“憲”行記》法治教育實踐教材,讓學生利用春秋假走入“五四憲法”歷史資料陳列館、政務服務大廳、社區居委會等,通過沉浸式、體驗式、合作式的學習參與法治實踐,增強憲法意識,培養法治精神。“唯有打通‘學校課程設計-文旅資源適配-家長權益保障’的閉環,才能讓春秋假真正發揮作用。”費丹艷說。
多位受訪者建議,春秋假應嵌入學校課程體系,并將研學活動主題與學科知識相結合,使學生在真實情境中深化理解。如設計分層活動,低年級側重興趣與生活體驗,高年級則強調探究與社會實踐,建立綜合評價機制以考察實踐效果。
此外,春秋假時間安排應結合地域氣候、文化與產業資源,形成地方特色。同時,直面城鄉差距,開展普惠性公益項目,確保農村學生和困難群體學生也能獲得高質量的春秋假體驗。
“重慶是一座山水之城,我們正計劃結合重慶地域特色,設計以‘自然教育與人文體驗’為核心的春秋假方案。”重慶兩江新區童心青禾小學黨支部書記、校長秦波建議,賦予學校更多自主權,允許其根據地域特點和自身條件靈活安排假期時間和活動內容,避免“一刀切”。如農村學校可側重農耕體驗,城市學校可側重科技與文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