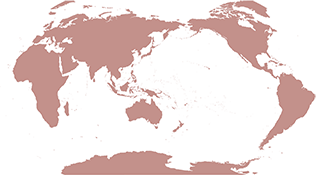

半月談評論員 毛振華 宋瑞
人到暮年,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伴隨社會的老齡化和少子化,遺產無人繼承的情況顯著增多,遺產處置的復雜性呈上升趨勢。在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及基層處置日益規范的當下,無主遺產處置的狀況得到極大改善,不但糾紛風險減少,而且越來越多的無主遺產轉化為社會財富,造福養老、教育、扶貧等公共事業,無形中也了卻故去者的心愿。
無主遺產不能成為“燙手山芋”
北京的張女士因病離世留下100多萬元財產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張女士多位親戚訴至法庭要求分割全部遺產,最終,法院判定100多萬元歸親戚,房產則收歸國有。無獨有偶,上海一位老人意外猝死后留下430萬元和一套房產無人繼承,最后法院判定分給老人堂弟130萬元,其余遺產也收歸國有。
獨居老人離世后留下大筆遺產,究竟由誰來繼承,往往成為爭議的焦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原則上歸國家所有,用于公益事業;若被繼承人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則遺產歸該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但在現實生活中,處置起來往往并不簡單。
有基層干部透露,有孤老將房屋鑰匙留給居委會書記保管,卻在未留遺囑的情況下驟然離世。這幢房子就此成了“燙手山芋”,既不能買賣也不能出租,只好無限期上鎖空置,久而久之愈發破敗。
北京卓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孫志峰指出,無主遺產常見的是由遺產所在地村民委員會或民政部門接管并處理,但接管后依然面臨難題。首先是缺乏必要的認定和接管程序;其次是基層管理處置隨意,缺乏統一協調的管理制度;還有就是基層組織缺乏專業人才。
“老齡化與少子化決定了無主遺產的案件數量以及所涉金額都會急劇增加,對無主遺產進行規范化與程序化管理越來越有必要性。”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洪波說。
當法規落到實操層面,遇上的難題遠比想象中要多。此時,對無主遺產的管理更為精細化就變得尤為重要。北京大成(太原)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燕認為,此舉一是為了避免社會資源浪費,將無主遺產轉化為公共服務資金;二是保障潛在繼承人(如遠親、非婚生子女等)的合法權益;三是防止遺產被濫用或流失,提升政府公信力;四是通過規范化管理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體現法治進步。
精細化管理的必要性源于深刻的社會變遷和法治需求。明確的管理流程可以保障遺產債務的清償、扶養人權利的實現,避免糾紛,維護各方主體的合法權利,而且有助于盤活社會資源,助力公益事業,最終將造福社會。
構建全鏈條法律框架
2021年,我國民法典首次確立遺產管理人制度,規定可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民政部門、村委會等擔任,如有爭議時,利害關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請指定遺產管理人。
與此相呼應,2024年1月1日起,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引入遺產管理人制度,在“特別程序”中新增一節“指定遺產管理人案件”,對遺產管理人案件管轄、申請要求、審查標準、救濟渠道等作出進一步規定。這些規定讓無主遺產的處置有了可操作的依據。

此外,考慮到無人承受遺產由國家無償取得,本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民法典第1160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32條的基礎上增加了對無人承受遺產歸國家所有后的用途限制,即應當用于公益事業。
遺產管理人制度的提出解決了“誰來管”的核心問題,負責清算、債務清償、保管遺產,職責法定化。制度的核心改變在于從無主遺產“被動閑置”到“主動管理”的轉變,構建起全鏈條法律框架。
張洪波表示,這些新規體現了我國在立法上對于無主遺產的處理較為重視。張燕也認為,新政策帶來了多方面改變:確立了民政部門或村委會為法定遺產管理人,具備法律主體地位;設立一年公告期,保障繼承人知情權和申報權;遺產最終歸國家或集體,歸國家的部分專項用于養老、教育、扶貧等公益事業;部分地區試點“遺產管理人名錄制度”,引入律師、會計師等專業力量參與管理。這些無疑都體現了司法的進步。
2024年,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依法適用特別程序,審結一起申請指定遺產管理人糾紛案件。在案件中,李某與張某簽訂了《借款協議》,約定李某要向張某償還123萬元借款,如果無法到期還款,愿意將自己名下房屋等資產作為抵押。李某因車禍去世后,張某找到李某妻子、女兒及姐姐,要求她們在繼承遺產的范圍內償還借款,但李某的全部繼承人均表示放棄繼承遺產。最終,法院判決李某生前所在的通州區永樂店鎮某村村民委員會為遺產管理人,負責被繼承人遺產的管理與清算,用于償還債務。
強化管理,確保有效執行
盡管民法典和民事訴訟法對無主遺產處置的法律規定不斷完善,但當下無主遺產認定程序仍有待完善。
其中,無主遺產是清償完債務并分配給酌情分得遺產人后的資產,但不論是民政部門還是村民委員會擔任遺產管理人,都缺乏對遺產以及酌情分得遺產人、遺產債務人等的相應的調查權限;法院有相應權限,然而民事訴訟法關于無主遺產程序中只規定有為期一年的公告,并未規定相應的調查程序。而且,缺乏清算程序。實踐中,有物業協助民政部門處理被繼承人的喪葬事宜,并且墊付了相應費用,卻無法從無主遺產中獲得相應的償付,也沒有其他主體支付相應費用。除此之外,無主遺產公益目的的實現缺乏監督,由村委會或社區層面處置后,公益資金使用缺乏透明度和審計保障,存在挪用風險。
天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曾艷提出,民政部門擔任遺產管理人存在一定的履職困難。隨著遺產形式的多元化(如知識產權、信托受益權、數字遺產等),對遺產管理人專業能力和資金保障要求日益提升。基層民政部門本職工作已很繁重,很難有更多精力處理復雜的遺產管理事務。

因此,除了法律法規層面的完善外,首先要從源頭充分盤活資源。天津吉賢律師事務所主任李邠彧認為,可建立統一的“無主遺產信息公示與查詢系統”,并探索與公安、出入境、外匯管理、金融機構的協作機制,追溯資產和繼承人線索,提升跨境協查效率。
在處置無主遺產時,要對民政部門如何履職予以明確并給予一定保障,并不斷提升基層專業管理能力。同時,對無主遺產作為公益資金使用的,須完善監督機制。李邠彧提出,建立從遺產清理、變現到資金入庫、使用的全流程記錄與公示制度。強制要求對接收遺產的公益基金進行年度專項審計,并公開審計結果,接受社會監督。通過多措并舉,推動無主遺產繼承制度實現從“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跨越。